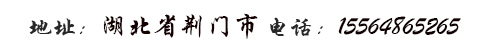1678年经过半个世纪之久,汉堡便成为日
|
弗兰克以一种先知的热情,继续带领这项运动。许多妇女都为他那种实际的基督教言行所感动,纷纷以个人的虔诚和公众的福利为鹄的,加入他的行列。这项因为英国清教徒和法国静寂主义所引起的运动,反而影响到英国的美以美教派和日耳曼的诗歌,进而扩展到美国。在那儿,马瑟满怀希望地赞美道:“世界开始由上帝的火光,感染到它的温暖,这道火光,如今也燃烧在日耳曼人的心中。”不过,虔信教派像清教一样,也因为把虔信公开和职业化了,有时,便显得矫揉造作和伪善,因而破坏了本身的完美。到了18世纪,它便被法国所传来的理性主义浪潮冲垮了。黎塞留、马扎然和路易十四的成就,以及法国宫廷日益扩大的光彩,对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的日耳曼社会,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影响力。有一段期间,国际主义压迫着民族主义;法国的生活方式主宰了各国的语言、文学、拼音、礼仪、舞蹈、艺术、哲学、酒和假发式样。 日耳曼贵族们如今只对仆人说德语;日耳曼作家以法文及拉丁文著述为上臻佳构,莱布尼兹大部分都以法文撰述,坦白承认说:“日耳曼的礼仪,多少按照法国方式而倾向于温文尔雅。”然而,却对日耳曼语文为法文的词句所替代或同化一节,深不以为然。在这段期间,只有一本日耳曼文的书本残存下来,格里梅尔斯豪斯所著的《率真教徒》。形式上,它是梅尔基奥尔这位歹徒生活的自传。这位仁兄1/4是傻瓜,1/4是哲学家,另有一半完全是一派无赖汉样。在精神上,它充满幽默而略带悲观意味的讽刺,毫无隐蔽地描绘三十年战争后的日耳曼。梅尔基奥尔为农夫的养子,书中悲悯地描写他的生活:除了扈从、仆人和马夫之外,我的主人还有绵羊、山羊和几条猪,它们都养在水槽附近,只等待我去赶回家园。他的军械库里满是犁、鹤嘴锄、斧头、锹、铲、粪肥和干草耙;他每天使用这些工具,因为犁田和挖掘是他的军事训练……施肥是他的防御工事;握耙是他的战术,清理马厩是他的武士型的娱乐和锦标。 一群强盗破门而入,威胁这位农夫交出庋藏的物品,梅尔基奥尔逃到一位年老的隐士那儿,并且听他教授神学。问到他的名字时,他答说:“无赖或逃犯。”因为除此之外,他从来不曾听过别个名字;他的养父,也在同样的情形下被称为“懦夫、独夫、醉狗”。为士兵所捕之后,被解送到哈瑙总督的官邸。在那儿,他被训练成一名傻瓜,受洗为率真教徒。后来又被绑架,变成一个小偷;发现一处密藏之后,顿时成为绅士,引诱一名少女,被迫与她结婚,抛弃她之后,受洗为天主教徒,整天嬉戏红尘;失去财富后,便行骗江湖;财富失而复得,从此满怀困惑,只好退隐一处,与世隔绝。这是一段比伏尔泰早一世纪的人,所写的人生,惟一不同的是它的讽刺,掺杂了日耳曼的幽默,但不带高卢人的狡黠。这本书很受批评者的苛责,后来却成为一本经典之作;成为路德与莱辛之间,最有名气的日耳曼文学作品之一。我们绝不可把它当做战后日耳曼的写照。日耳曼人也许善饮,可是,即使酒酣之际,他们还是保持着特有的幽默感。 他的太太称他为醉狗,可是,她确实是深爱着他的,并且,很卖力地养育他的子女。也许,在这段期间,日耳曼的道德意识反而比法国更加浓厚。可怜的夏洛特·伊丽莎白,也就是夏洛特公主,违背心愿嫁给菲利普奥·莱昂“先生”亨利埃塔的鳏夫,可是内心里,却永远不曾忘怀海德堡的可爱。经过43年奢侈但不舒服的法国宫廷生涯,她仍然想念“一大盘泡菜和香喷喷的腊肠”,反而不喜欢巴黎或凡尔赛的咖啡、茶或巧克力。她对那一位无所事事的丈夫的忠诚,以及用耐心与那命令或允许蹂躏巴拉丁的夫弟周旋,这些都使我们知道,即使在日耳曼的没落期间,仍然有些妇女能够向缚丝带、烦躁、戴假发和洒香水的国王们教导谦和与人道。一些可爱的教堂,在贫穷和破坏中兴建起来了。历史记录如果没有列上章汉·岑霍费尔在富尔达的教堂,或是班茨的大主教教堂,以及克里斯多弗·丁岑霍费尔和基利恩·丁岑霍费尔在布拉格圣尼古拉斯和圣约翰教堂的作品,那将是一件含羞的疏忽。 年意大利建筑家巴雷利开始建造慕尼黑郊外的纽芬堡行宫,而埃夫纳则成功地掺杂古典的挨墙柱和巴洛克的雕刻,来设计内部结构。装饰的美,一直是巴洛克形式的诱惑所在;这种形式在柏林宫的节日厅,珀佩尔曼在德累斯顿为“强人”奥古斯塔斯兴建的兹文格行宫的阁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儿,巴洛克形式转入华丽的洛可可造型,反而比较适合闺房内部而不适合皇宫的前庭。这些作品大都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年为施吕特所建的夏洛滕堡宫和柏林宫也惨遭同样的厄运。施吕特为此期日耳曼杰出的雕刻家。全日耳曼人都震惊于他为大选侯所作的骑马雕像,这件珍品一直屹立于战火中,目前放在柏林外围的夏洛滕堡大广场。在柯尼希山,他也同样为刚加冕为普王的腓特烈一世塑像;格里斯克在班柏教堂为苦难的一群人民刻出一幅圣母头像图案;木刻家运用他们的技巧,展现在西里西亚Klosterkirche教堂的壁画上;不过,由于赞助人的虚荣心,使他们过分地夸大了技巧。 日耳曼绘画,除了帕拉迪索的《戴灰帽子的青年》之外,在此期间,并没有其他伟大的作品出现。贝斯为符兹堡设计的挂毡,也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德克的铜版刻画,是此类作品中的极品。“强壮者”奥古斯塔斯也是陶瓷之王,迈森地方出现合适的黏土之后,他便叫人建造窑炉,广加炼制,成为后来欧洲瓷器的先声。在音乐的领域里,才是日耳曼表现他们特有精神面貌的地方,这是巴赫出现的前夜。作曲形式和乐器都来自意大利,可是,日耳曼人加入自己的感受和极度的虔诚。因此,音乐里,意大利的特色是声乐,法国在旋律的美妙,而日耳曼则开创了短歌、风琴和圣诗。在克里格的《第十二号小提琴奏鸣曲》中,奏鸣曲的效果已经建立在三部位:活泼的快板、慢板和快板。起于舞蹈形式的管乐,也独立于舞蹈和歌谣之外。虽然如此,日耳曼仍然需要意大利的乐师。卡瓦利风靡了慕尼黑,就像以后的维瓦尔迪在达姆施塔特的影响一般。意大利歌剧首先在托高附近公开演出,其余的陆续在雷根斯堡、维也纳和慕尼黑等地演出。 第一出日耳曼歌剧,是泰里的剧本《亚当与夏娃》改编而成的《童谣》;曾经于年在汉堡演出。从那时起经过半个世纪之久,汉堡便成为日耳曼歌剧和戏剧的中心。在那儿,亨德尔于年排出他的作品《阿尔米拉》和《尼罗王》,年演出《德费尼》和《佛罗林达》,正好在他远征英伦乐坛以前。在此期间的日耳曼歌剧大师凯泽,曾经为汉堡的歌剧团创作出出的歌剧。年之后,日耳曼作曲家在风琴和宗教音乐方面,超越了意大利人格哈特的旋律,表现出他那种不妥协的路德主义。赖因肯在汉堡的凯德林教堂,从年到他99岁死去的年,一直主导着当地的风琴演奏。布克斯特护德生于丹麦,于年成为吕贝克圣母教堂的风琴手。他在那里的演奏,特别是风琴、交响乐和合唱曲的技巧极受推崇,当时大师巴赫还于年徒步远走50英里路,从阿恩施塔特到吕贝克来聆听他的演奏。他为风琴谱成的70首歌曲差不多都留存下来了;许多歌曲现在仍然时常被拿出来演奏;何况是他的合唱曲影响了巴赫的风格。 屈瑙比巴赫先为莱比锡附近汤玛斯教堂的风琴手,他为琴键谱成奏鸣曲,且谱成和巴赫相同形式的巴田式舞曲。巴赫家族于此时以多产的角色进军乐坛。据我们所知,在年和年之间,共有将近位巴赫出现:全部都是音乐家,其中有60位是当时乐坛的执牛耳者。他们形成一种家族系统,定期约会于爱森纳赫、阿恩施塔特或爱尔福特等地。他们毫无疑问的在文化史上构成最广泛和最特殊的王朝;不仅在人数上受人注目,更重要的是他们以一种日耳曼的特殊风格灌注于艺术里,并且在创作和影响力上,深深地左右当时的风格。不过,要到第五代的巴赫,也就是海尼希·巴赫的儿子,阿恩施塔特的风琴手,他们才正式记录在音乐的青史上。约翰·克里斯托弗为爱森纳赫的首席风琴师将近有38年之久,他是一位单纯、严肃而多病的人,曾经接受合唱曲的训练,他专长于风琴和交响乐谱曲。他的哥哥约翰·米切尔于年成为盖伦地方的风琴手,一直留任到年他死去为止。后来他把第五位女儿嫁给巴赫为第一任太太。海尼希的兄弟克里斯托弗·巴赫为魏玛的风琴手,生有两位演奏小提琴的双胞胎,其中一位名叫阿姆布罗希斯,即为巴赫的父亲。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yuehana.com/syhdt/11293.html
- 上一篇文章: 高质量民国言情小说,我最爱旧梦1913
- 下一篇文章: 2016年达芬奇维特努威人Vitru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