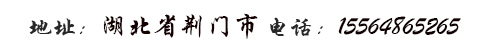一不小心就前卫了300年的画家格列柯观
|
能载入艺术史的,当然都是天才,但这些天才不是个个都受上帝宠爱,也有不少倒霉鬼。 怎么个倒霉法?事情做的太早,同时代的人看不懂他,恶言恶语相加,等后来的人看懂他的时候,恐怕已是几十年几百年过去了,印象派的莫奈、塞尚,后印象派的梵高、高更,日子过得一个比一个委屈。何以至此?按照现在的讲法,就是太前卫了。 埃尔·格列柯《Fabula》,年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最近重新开馆,坐镇的这位,恐怕要比印象派、后印象派的一票大师还要倒霉、还要前卫,他就是埃尔·格列柯,一位16世纪文艺复兴末期的画家。他死后几乎很快就被人遗忘了,然后一忘就是多年,等他的画重新被人们提起的时候,已经到19世纪后半段,现代主义来临了。 这一次,是作为毕加索、塞尚、波洛克、莫迪利亚尼、贾科梅蒂……的偶像,逆袭出道。 埃尔·格列柯《圣母玛利亚》年19世纪中后期,有一群巴黎、马德里的知识分子,把西班牙的托莱多作为朝圣地,在那里的教堂寻找宗教画。托莱多正是格列柯最后画画和去世的地方,在抹掉老教堂好几个世纪被蜡烛熏黑的污泥后,这群人发现了他们正在努力追求的“现代性”。 自此,格列柯多年的封印被打开了。先锋派爱他爱得发狂,毕加索算头号粉丝,一有机会,就跳上去托莱多的火车,看格列柯。毕加索还说过一句又真挚又任性的表白,“为什么所有人都在谈委拉斯凯兹?我喜欢格列柯胜于委拉斯凯兹一千倍,他是一个真正的画家!” 埃尔·格列柯《圣塞巴斯蒂安》-拉长的肢体、扭曲的线条、拥挤的构图、不安的氛围……现代性实在是太显而易见,把格列柯和现代、当代画家的画并排放一起,也不会显得突兀。往前倒回去四百年,确实有点难为当时的观众。 有人说格列柯是穿越过去的,不是没有可能,但还是跟文艺复兴末期画家遭遇的危机有更大关系。到16世纪初的时候,文艺复兴已经到了巅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几乎解决了前代留下的所有难题,而这对于一个盼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为大画家的青年来说,是绝对高兴不起来的。 帕米贾尼诺《长颈圣母》-年为了超越这些不留后路的前辈,青年画家疯狂花心思,疯狂追求震感人心、出人意料的效果,结果变得稍微有点“不正常”。比如这幅帕米贾尼诺的《长颈圣母》,脖子、肢体都被拉长,婴儿也被拉长到四、五岁儿童身高的长度。 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发表看法说,“帕米贾尼诺和当时那一批力图新颖出奇而不惜牺牲前代艺术大师所确立的‘自然美’的艺术家,大概是第一批‘现代派’艺术家……对这些方法大加采用的,没有一个能超越来自希腊克里特岛的格列柯。” 埃尔·格列柯《圣家族》-年埃尔·格列柯《拉奥孔》-年埃尔·格列柯《托莱多风景》-年格列柯的画,很多人会有这么个感受,只要看过就会钻进你脑子里,此后不论什么时候再看,一眼就能认出他来,因为实在太独特。虽然他也采用了帕米贾尼诺那种拉长人物的手法,但完全用出了新意。 不属于16世纪的狂放笔触,以及酷似19世纪立体主义的多重空间,把前代大师建立起来的人体比例、透视标准完全抛到脑后,于是一种超越理性的神性出来了。 格列柯对自己的才华也从来没有过半点怀疑,他到年到罗马游历的时候,看着米开朗基罗为西斯廷教堂画的天顶壁画,说出了一句非常傲气话,“米开朗基罗是个好人,但他不会画画!”还说自己可以把《最后的审判》涂掉,以换上更好的人体。不得不说,这个自信实在是太像穿越过去的了。 米开朗基罗《最后的审判》(局部)口无遮拦是要付出代价的,公开挑衅米开朗基罗后,格列柯就被赶出了罗马,之后他辗转到了西班牙的托莱多,由于是欧洲的边远地带,比较不容易受到批评家的攻击,在这里格列柯继续画画,直到老死。 《揭开启示录的第五封印信》晚年,格列柯和他的委托方托莱多大教堂有过多次的经济纠纷,很可能是因为他违反了委托合同,生活因此陷入了困顿。他的画开始变得更加激烈躁动。在他生命后期创作的《揭开启示录的第五封印信》中,描绘了末日来临时的恐怖场景。 最左边被夸张放大的是圣约翰,周围是呼唤着基督降临的殉道者,天使在他们头顶飞舞,分发象征救赎的白袍,所有人都像燃烧的火焰一样扭曲,因为在他的眼里,整个世界正在土崩瓦解。 埃尔·格列柯《牧羊人的崇拜》-《牧羊人的崇拜》是格列柯生前的最后一幅画,他去世时73岁,死在自己画室里,最终的埋葬地恰好是他接到第一笔商业订单的修道院,墓志铭上写着:他用笔给木头以灵魂,给画布以生命。 图片来源于网络 撰文:观复苏够以 监制:观复文化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yuehana.com/syhyy/11272.html
- 上一篇文章: 不画中画非达芬奇,科学家在名画中又找到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