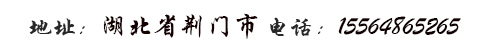孙立人秘书黄美之现在的大学生和民国大学生
|
最好白癜风专科医院 http://m.39.net/pf/a_4487554.html 明凤英文 黄美之的名字不为人所知,但她的经历却串起一段传奇的近代史。她的表舅是著名报人成舍我,表哥是经济学者成思危,她母亲的同学兼好友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向警予。她本人曾任抗日名将孙立人的秘书,与之发展出一段感情,并受孙立人案牵连入狱十年。年,定居美国的黄美之与她的朋友、旅美学者明凤英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对谈,回顾自己动荡而精彩的一生,这也是她生前最后的访谈。年7月16日,她在美国的家中离世。本文为访谈节选。简介黄美之(-),旅美作家,学名黄正。出生于湖南长沙,南京金陵女大历史系肄业。年初到台湾时,曾短期任抗日名将孙立人将军英文秘书,并在其“女青年大队”工作,与孙立人将军有过一段乱世情缘。当时黄20岁,孙50岁。年,她与姐姐黄珏以“泄露军机”罪名,双双入狱,在牢中度过10年。出狱后曾任复兴电台编辑,台湾“内政部”国际劳工组织员。年与美籍外交官傅礼士结婚。年后开始小说散文创作。著有游记《八千里路云和月》、短篇小说《流转》、散文集《伤痕》等。对民国时期大学校园的回忆 明凤英:您和姐姐都考入当时教会办的私立贵族学校,有名的金陵女大。民国时期的大学校园是怎么样的?学生想的都是什么?有什么特别的人物和趣事吗? 黄美之:当时在北京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有:南开大学。上海有: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南京有: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般称为金陵女大。武昌有武汉大学,广州有中山大学、岭南大学,重庆有四川大学,成都有华西大学。中央大学在南京,是很好的。中央政治大学更难进,是国民党党校,成绩要很好的人才能进去念书,一毛钱学费都不用缴,以后是要派出去做干部,做官的。长沙有湖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那是美国耶鲁大学的分院。医院医院。设备很好。战时湘雅医学院曾搬去贵州,战后又搬回长沙,仍是医院。 抗战时期,有名的大学都迁移至大后方。北京、清华和南开这三个大学,在昆明合为有名的西南联大。重庆沙坪坝有中央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和几个教会办的学校,包括北京的燕京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大,都搬到成都去了。都位于成都华西坝,与华西大学校园在一起。华西大学也是教会学校,教会大学学费不便宜,算是贵族学校。每个学校虽在同一个区,但各做各的。 那真是年轻大学生的黄金时代。日本人好像也没有炸到成都去,大家都穿得漂漂亮亮,骑个脚踏车,很好看。那时候真是不一样。我是抗战胜利以后啊,才有机会去看看。我姐姐当时正进入金陵女大,我去看过她一次,好大一片地方。华西大学校园很美,地方很大,上海医学院也在那里,和华西医学院合并。 年秋天,我跟我姐姐又回去看了一次,可是已经整个不一样了。医学院的学生一面走路一面吃饭,已经没有当年年轻人的好看。那时候大家讲究穿着和manner(举止、礼貌)。现在那个时代已经没有了。 明凤英:当时的大学生在战乱中求学,他们所思所想,跟现代年轻人不一样吧? 黄美之:我不知道我这一代的人幸还是不幸,反正是在战乱中成长的。有好吃好玩时,会及时行乐,很自立。时局乱了,也能镇定以对,反正有父母可靠嘛。我们这一代真正是在内外战争中成长的,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有了一种及时行乐的悠然,因为那个时代真正变化莫测,也看不到未来会是什么。至少我是糊糊涂涂不闻不问地过那年轻人天真无邪的快乐日子。我认识的同学都是这样。因为内战的战火并没有真正逼到我们身边来,真正南京危险的时候,我们已经都跑掉了。很多都是国民党的家属,跑得快! 不过,那时候,我们大学生常有“反饥饿大游行”,公立学校真的开不出饭来。他们的钱,政府按月给。但是我们金陵女大是私立教会学校,学费是一开学就缴了。他们把米什么的,一开始就买好了。最苦的时候,我们本是四个菜,只是改成两个菜而已。我们的学校,就是美国SmithCollege的姐妹校。学校不大,几百个人而已。哈金写的那本《南京挽歌》(NanjingRequiem)。就是以金陵女大为背景的。还有一张金陵女大的地图。宫廷式的建筑,现在还是那个样子,去年我去过一次,仍叫金陵女子学院,但属于南京师范学院的行政体系。 明凤英:男女学生的交往很自由开放吗? 黄美之:很自由的,好像我们金陵女大的,差不多都有男朋友。一下课,就有男生站在门口等。我们跳舞,多半在同学家里,大官小孩的家。我们还蛮会打扮的,那时我们已扎马尾,在学校穿平底鞋,出去就穿高跟鞋。我从小就喜欢跳舞,也没怎么学,就会了。大学时候大概跟男朋友跳,很快就会了。后来南京乱了,不能读书了,中山大学可以接受我们这些学生,我就去了广州。那时候,还有不少同学也是从南京去的,有朋友。哎呀,真是好玩。所以,我虽然坐了10年牢,但是坐牢以前还是玩得蛮过瘾的。 明凤英:有人说民国时代的人,风度品位是很不错的。 黄美之:我想当时若没有战争,中国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那时候封建势力的旧习惯还有些存在,而且还讲究排场。我想,穿着、仪态、manner,都是重要的。现在,凭良心讲,大多数人是没有什么派头的。民国时候的那些清朝的官派还是留下来一些派头,还有学者们也是。 我姐姐那个时代,仪态、穿着、走路、讲话都是有指导的。比如上一届的学长怎么做,讲究风度,下面的学妹也就不能太随便了,自然而然就有了一种风气。 在金陵女大时,黄美之穿着自己做的衣服。 黄美之和姐姐黄珏。 明凤英:刚才您说抗战时候大学生玩得厉害。我以前听见人说八年抗战,都是物资匮乏,生活艰苦啊。 黄美之:八年抗战时是很苦,但我这一代尚在中学,而中学都在很宁静不愁吃穿的乡下。至于那些大学生,相反的,他们生活虽清苦,仍是充满了希望和快乐哩。年冬天,局势就开始紧张了,考试也就马马虎虎了。日子过得糊里糊涂的。年冬天,那就很紧张了。从年到年,我们及时行乐,但是那时候我们确实也好可怜,不知道做什么好,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大家在那里讲谁谁谁要到台湾去。记得有一个同学说她不能去,她的父亲被调到重庆去了,她也要去。不久就听说重庆大火,不晓得他们怎么样了。我们大学生就逃难,有的去了广州中山大学,也有人去广州的岭南大学。我们金陵女大所有的文件都早送到SmithCollege去了,所以其实学校早就知道政治上的局势了,只是我们学生傻乎乎的不知道而已。 明凤英:及时行乐的背后,是严酷的战争。 黄美之:大学生当然知道时局很乱,很担忧,但也不知道做什么。又担忧,又及时行乐。我从小就经历战乱,先是抗战,后来是国共内战,所以也习惯了。反正不来轰炸我们就做自己的事,来轰炸了,我们就跑。习惯了。 国民党政府搬到广州,第一个承认共产党的就是英国,可是他们又刚刚才送了两条兵舰给国民政府。有一个小一点的舰,就叫“灵甫舰”。那时候国际政治就是这样。张灵甫,在山东被共产党包围,打不过,就自杀了。他是美男子,太太很年轻,才17岁,肚子里怀着孩子。老蒋最喜欢他,纪念他,就是因为他自杀,后来孙立人有几个部下从大陆回台湾来,老蒋把他们关起来,说,人家张灵甫能自杀,你怎么不自杀?那几个人是打不过被俘虏的,后来到了台湾。 老蒋那时候,总叫人为国捐躯,他自己不也是往台湾跑?他到台湾的时候,军舰在海上转来转去不敢登陆。陈诚告诉他,那时候还不安全,不能登陆。老蒋打电话给孙立人,孙立人说,你走高雄码头上来,我亲自到码头去接你。你看,后来老蒋却把他软禁了30多年。无毒不丈夫啊。 孙立人将军。 与孙立人将军的一段情 明凤英:时隔多年,您在80岁那年出版《烽火俪人》,以小说的文体写出60年前,在国共政治党派纠结,各派势力缠斗的氛围里,与孙立人将军不为人知的一段情。这段恋情公开之后,各方的舆论和压力想必不小? 黄美之:我是80岁后才写《烽火俪人》的,写我那段青春岁月的茫然和奇妙的甜与苦。我写《烽火俪人》不是未经考虑的,也许因为年纪大了,回看那一点情,也是温暖令人难割舍的。写下来就没有遗憾了。一种真正的放下和解脱。我很客观地认为我能十分冷静的来面对那段理还乱的情绪了。这书我本名为《小楼札记》,但出版社说这样的书名不会有吸引力,坚持要换成《烽火俪人》。我当然只有听从专家的话,有一些可爱的好心人很欣赏我的作品。他们是真正站在一种情的定位上来看我的这本书的。 明凤英:可以多跟您谈谈这段感情吗?您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当初和孙立人将军的感情,是少女的“醉了,但是醒来却很痛苦”。 黄美之:爱情确实是一个让人迷惘的问题,很多人活了一辈子,也还弄不清爱情到底是什么。但我觉得在台湾那栋小楼里的一段时间,是很值得珍惜的。我想孙将军也应该很珍惜那段在小楼的岁月。 明凤英:战乱的年代,年轻女子求生存,寻找自保,爱情是不是很脆弱呢?是不是身不由己,自己也不能完全掌握呢?您描述到故事里的女主人翁感到迷惑,似乎有罪恶感,也不知道该称呼自己喜欢的人为长辈、情人,还是将军。您那时候是不是也感受到道德的困境呢? 黄美之:乱世里,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命运和际遇。这不只是情欲和虚荣心的故事。每个人带着各自不同的背景和故事,在那历史的时空里,有一个交集。这个短暂的刹那和缘分过去以后,故事也就消散了。我原来的书名,是《小楼札记》。到现在,我都还很珍惜那段日子。我很崇敬孙立人将军,而对戎马生涯的孙将军来说,我大概也是新鲜的空气吧。 孙立人将军和妻子张晶英。 孙立人将军是有家室的人。孙太太好几次跟我说,她是不会离婚的。她说在台湾,除了孙立人是她的丈夫之外,她一个亲人都没有。我听了非常难过,身为女人我当然是同情她的。所以我想我一定要离开,走得远远的,最好是出国。他是个可爱的男人,说我不爱他,那是假的。但我是读过书的,有年轻学生的志气,绝不能当人家的姨太太。孙将军是有道义的人。但是,我很痛苦,也想过自杀,干脆死掉算了。 明凤英:那个时代的感情,有特殊的时代背景。 黄美之:时局混乱,战争和新旧交接的时代,一切都很迷惘失望。是的。他给我一种安全感。再说,20岁左右,懵懵懂懂,谁真的懂爱情?那时候只要你跟一个男人跳舞,别人就说那是你的男朋友。回头看,上帝对我也还不错。在牢里关了十年,后来跟Bob结婚以后,全世界到处跑,也好好玩了十年,算是弥补过来了。你关我十年,我就玩你十年,也不算吃亏。只能这么想。 明凤英:您觉得自己是个有韧性的人吗?您似乎总能在人生的某个死角,发现生机? 黄美之:有人在我的网上骂我,我也无所谓。因他们并不是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况。但多半是一些年轻读者,如我当年那样年轻的人,欣赏我的作品。他们是真正站在一种情的定位上来看我的这本书的,是真正懂得情和爱的有文学爱好的人。我也不生那几位骂我的人的气,因这些人会是从道德的观点出发的。我并不以我这段情自豪,心中总有份怜恤。一位在复杂的政治情况中,曾经坦荡的,为国拼命流血的将军的寂寥,我并不真正了解,但总为他有所牵挂。年,也许是年,他调成参军长后,定有所觉,送了三百元台币给在牢中的李鸿将军,三百元给陈鸣人将军,还有所有跟李鸿将军一同坐牢的军人。他们都住在我和姐姐的隔室。我和姐姐便很不平地说,奇怪了,为何不给我们两人呀? 但他要陈良埙把他唯一的一本Gen.JosephW.Stilwell写的《TheStilwellPapers》送到我妈妈家,要我妈妈转寄给我们。我们收到那本书便很生气,说谁要看这书。但我稍稍翻一下,就明白了。他要我们知道,他曾为国家,为世界都出过力的。因此,我一直好好地保护着这书。若看守长来查牢房时,我便把这书放在枕头下。其实那看守长是一个很知情达理的人,这书既可送进来,便不是禁书了,何况是英文的。 女作家赵淑敏教授曾跟我说:“你还可以和一些人谈谈你心中的委屈,但不管他(孙立人将军)身边有什么人,都无法提及你们两人的那段情,和他深心内的那种牵挂。”是吗?淑敏,我相信你是对的。若他的家人想要把这本书要回去,放在他的纪念馆,我也很愿物还原主。只请不要把我留在上面的字涂抺掉了。 明凤英:现在回顾,还是感慨? 黄美之:当年,我母亲和姐姐很顺利地到了屏东,一切都充满了阳光似的,却没想到结果是如此不堪。我和姐姐莫名其妙地坐了十年的黑牢。父亲匆忙来到台湾,见到我们的情况,竟是束手无策,就急死了。我母亲独自承担一切。 回想那年我到屏东不久,有一次随车去火车站接从台北回来的孙将军。他坐进车时,一语不发,车开后,突叹了口气说道:“就是找不到学儿童福利的人,托人在台北找了这么久,也找不到。”我说,“我姐姐便是学儿童福利的,才毕业。”“在哪儿?”他惊讶地掉转头来问我。我说:“她在广州的联合国儿童福利园工作。”他惊喜地道:“快请她来。陈参谋,快打电报去广州办事处,去请她来,她住在什么地方?”我说:“那儿童福利园的地址我不记得了,早两天你不在家时,我的侄女婿王军长来过,说我的母亲已到了广州,现在我姐姐陪我妈妈住在爱群酒家。”“那好找。”他马上吩咐坐在前面的陈参谋快打电报去广州办事处,把她们母女找到,即刻送来台湾。 我急着说:“快呀快呀。”陈参谋笑道:“不问你还不说,现在又这样着急了。”“我不知道去哪儿申请入境证呐?早两天王军长才来告诉我的,说我妈妈只知道她家的四小姐是来台湾找他的,现在却杳无音讯了,因怕共产党马上会到广州,便预备先和另一太太去香港看看房子,真希望她们尚在广州。早不知道你们可以申请到入境证。”孙将军,陈参谋,连司机田排长也笑了。 年孙将军也被软禁,直到经国先生去世。现在一切落幕了,所幸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学者们,在朱浤源教授的引导下,为后人留下了这一本厚重的《孙立人上将项目追踪访谈录》。这是一段七彩缤纷的近代史。令人喝彩,也令人泪下如雨。 文章有删节,全文可点击阅读全文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yuehana.com/syhyy/8134.html
- 上一篇文章: 年5月6日星期四圣斯丹尼斯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