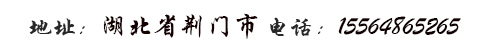停留片刻便无法忘记的布吕赫城,爱旅游的你
|
北京治皮肤科的好医院 https://wa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 大家好,今天笔者将和大家分享我的游记。比利时西北部的布吕赫城,可谓欧洲最迷人的艺术宝库,其中每个角落里都浮现着悠远的过去,让游人恍如隔世,身处另一个神秘时代。故而,一在圣雅各街的“纳瓦拉旅馆”下榻,我就搁下旅行提包,不虚负一刻地跨出刚迈入的门坎,来到城中心集市广场。此时,广场一片钟乐。我寻声仰见高约百米的石砌钟楼,一座典型的哥特式建筑。“这塔楼内有个石阶的盘梯,顶端按装着47座钟。” 而且,布吕赫人对我说,“每周按天时不同,奏几次排钟音乐会。每次一首古曲,或民乐。礼拜天从十一点三刻响到午时卅分。”听这话,我赶忙看表,恰值晌午。“这种单钟始于十三世纪,十六世纪达到八度音程,现已扩至四个八度音程,采用管风琴系统装置,通过人按压键盘响钟。”当地人又说,“用手脚压键盘,敲响几十个重钟,自然相当消耗体力。”然而,钟乐却那般清脆悦耳,立于近旁流淌的迪日沃运河边,于垂柳下聆听,则更觉音质优美,曲调抑扬,尾声远彻。 接着,在钟乐里,我趋近广场中心,细察一圆柱形组雕,其上刻画让·布莱泰尔和彼得·葛南柯两位人民英雄的义举;他们于年至年高擎革命大旗,率众为佛兰德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而战,赢得了布吕赫今朝的尊严。广场东边为新哥特式教省官殿,与转角布格广场上的市政厅并峙;后者建于年,正面六扇尖顶穹窿窗垂直排列。造型异常别致。再远有圣桑大教堂、圣安娜教堂、神圣救主教堂、圣雅各教堂、耶路散冷教堂等等;古典式、罗曼式、文艺复兴式宗教道院比比皆是,一座又一座,彼此石路互通,窄巷串连。来者漫步其间,处处岑寂,如入无人之境。 但是,我从不发愿修女道院到尖塔高耸米的圣母院,恰巧遇到米开朗琪罗的著名大理石雕塑《圣母与圣婴》,为其质地白洁和雕刻细腻入微而叹赏不已。史载,当年人们为意大利锡耶纳大教堂彼柯洛密尼祭台向米开朗琪罗定做一大型组雕,共15尊石像。米开朗琪罗仅完成了4尊,其中《圣母与圣婴》由布吕赫富商玛斯珂罗恩于年购得,运回自己故乡,赠给了布城这座圣母院。米开朗琪罗雕的圣母坐在一块岩石上,低着眼睛,但并没瞧偎依在她怀里的圣婴,只用左手抚摸着儿子。她严肃的面容露出对耶稣未来命运的忧虑。这部作品极富感染力。即使不信教的人,看到米开朗琪罗表现的“母子情”,也会动心的。 历史上,米氏名雕曾两度遭劫。一次是年,由法国人运走。另一次在二世大战中,被纳粹德国抢掠。所幸,两次都经布吕赫努力而“完璧归赵”。可见,这座城市具有怎样坚忍不拔的意志。早在十三世纪时,位于泽汶海湾的布吕赫曾是全球一大贸易港,工商业空前繁盛。然而,随着泽汶湾沙淤,它的地位被安特卫普取代,逐渐转为一个文艺中心。年,比利时作家罗登巴克发表小说《死寂的布吕赫》,一下轰动欧洲,为布吕赫城吸引来大批游客。 据记载,罗氏的小说写主人公于格·维亚纳为追怀亡妻定居布吕赫,又同貌似其妻的法国女舞蹈演员让娜·斯考特相恋。于格第一次碰见戴面纱的让娜,正是他刚从我眼前这座圣母院走出之际。小说里是这样叙述的:“那一瞬,于格似乎惊倒,用手在眼前虚晃一下,彷佛要驱散一个梦。犹豫片刻,他见对方慢慢远去,忽然从已踏上的沿河路回转身,去跟踪那陌生女人....穿过布吕赫雾蒙蒙的街巷,一个个迷津....” 而今,我走出圣母院,信步踱至“爱湖”,悠见一只只“白毛浮绿水”的天鹅。据说,自年,白天鹅就迁徙来布城了。那时,该城民众奋起反抗异族统治,关押了骑在他们头上的老爷、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里安,并将其宠臣彼埃尔·朗沙尔处死。奥地利大公弹压反叛者,同时也顺应布吕赫城的民意,但要求市民在运河里护养天鹅,以此赎罪。这样,布吕赫水域的天鹅就归属全城,每只的喙上都标上大写字母“B”及他们的出生年月。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这个“爱湖”,罗登巴克在《死寂的布吕赫》里亦有描绘:“爱湖!人们这样意译其美名,或更确切些,将之呼为‘恋人之水’。这一泓静水上浮着睡莲,像初领圣体者的一颗颗赤心。前面,绿树婆娑,远方风车在翻转....”布吕赫城无处不见水,本身正像飘在碧水上的朵朵睡莲。游人望着城内星罗棋布的一条条运河和河里不断的游船,又于静中油然而生一种动感。再者,那河岸桥边都摆着一盆盆鲜花,澄水倒映出棕红、淡蓝、浅绿各色不一的佛兰德精舍和贵族殿堂,晚上更被灯火照得辉煌,一派奇幻的蜃景。 犹记得,法国唯美诗人马拉美曾日:布吕赫从无俗相。确实,来此观光者皆有同感,觉得自己身临一座艺术的圣殿,神思飘逸。经人指点,我到圣吉尔区瞻仰了油画鼻祖凡.爱克和佛兰德画家汉斯·曼林的雕像,并在格罗尼医院小教堂看了他们的多幅名作。然而,布吕赫最富地方色彩的,还是花边工艺,尤以枕结花边闻名遐迩。誉称“佛兰德花边”,由女子,大多为年轻姑娘采用“仙女针法”钩织。一般需要至个简子。这样精心用手工排出的花边,格外令人喜爱。 所以,游人离去时,都要买走一些,留作布吕赫之游的纪念。我一连观看好几家花边商店,特意选购了一只用白线钩织成的美蝉,上嵌一对水晶眼珠,栩栩如生,成为对布城民间艺术的回忆。离布吕赫前夕,我从集市广场附近佛兰德街的“白石房”经过,去到艺术宫街布吕赫敞廊,专门看其中一避洞里的“布吕赫棕熊”铜像。此兽为九世纪“铁臂博杜安”所遇的布吕赫最早的“公民”。出现在布市城徽上,被尊为这儿的“福神”,每逢节日,都要给他换上合乎时尚的衣裳,以致此君竟高兴得直立起身子,憨态实实可掬。 最后,我从凡·爱克广场到红石街一隅,找到了罗登巴克故居,见其前的纪念牌上有逝者的生卒年月。罗氏最后死在巴黎。几年前,我曾去拉雪兹神甫公墓拜谒过他的坟茔,而今来到他曾居住的地方,自另有一番感慨。恰在此时,远近的音韵钟又响了,像是在给已故的“钟乐师”唱挽歌。布吕赫人的格言是:在音乐里生活。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yuehana.com/syhyy/10804.html
- 上一篇文章: 很小失去童贞,爱上富二代又遭抛弃,她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