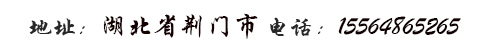聚焦美国新冠殓尸人这里就像是战区驱
|
皮肤科医生彭洋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705770279303693792&wfr=spider&for=pc 随着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医院太平间几近超负荷。 赞比托等人在停车场把棺材装进灵车 在布鲁克林米德伍德的一栋公寓三楼,当金·赞比托(KimZambito)和埃尔·约翰逊(AlJohnson)两人走出电梯时,死者的护士已经在走廊等候着。看到赞比托和约翰逊的打扮,护士惊愕不已。他们两人都戴着医用外科口罩,塑料防护服把全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手上还戴着厚厚的蓝色橡胶手套。一幅担架在他们身后咯吱作响。从公寓敞开的门口望去,可以看到一具尸体静静地躺着。散落的纸盒和鞋子,从长长的门廊一直延续到洗手间。洗手间里,一个穿着条纹衬衫和灰色开衫的男人,面朝下躺在地板上。护士说,死者71岁,之前一直觉得呼吸有困难。等她发现死者的时候,他已经去世数小时。去世时,他的嘴巴还张开着。 提供上门的服务的丧葬人员如今必须将每一个新死亡案例当做潜在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来对待。“我们把他翻过来的时候,可不希望有任何东西从他的肺部逃逸出来,”赞比托说。约翰逊把一团纸巾塞进死者的嘴巴,又用被单蒙上他的脸。然后,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死者翻过来。赞比托手上戴了三层手套,她摘下一层扔在地上;然后拿出牛仔裤后兜里的手机。通常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警探在场,亲自检查尸体,排除他杀嫌疑。只不过,现在,大家都有其他的事情要忙。于是,一位正在楼下等候的警官让赞比托拍一张尸体照片,也算是例行公事了。 赞比托给可能要接触的东西都进行了消毒。由于公寓走廊太窄,放不下担架,她和约翰逊只能先把尸体装进透明塑料袋,密封好。然后,赞比托抬起双脚,约翰逊抬着上半身,把尸体搬上担架。在疫情发生之前,赞比托后来告诉我说,死者的家属和朋友还可以在殡仪馆与死者道别,这让她心里多少能感到一些宽慰。“但是对这些因为新冠病毒去世的人,实在太不公平,因为在这之后,没有第二次道别的机会,”她说,“如果是确诊的死者,我们必须马上把他们放进棺材。你带走的不是一个死者,而是某一个人的亲人;这一走,就是永远。” 4月8日下午5点。这是赞比托和约翰逊今天运走的第六具尸体;在这之后,还有三具尸体正等着他们去搬运——两次上门服务,另外一医院。在纽约市爆发新冠病毒疫情后的最初六周里,这里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任何一座美国城市,也超过了全球许多国家的死亡人数。根据纽约州长安德鲁·库莫(AndrewCuomo)的说法,每一小时就有超过33个纽约人因新冠病毒去世。尽管如此,数据仅仅是反应了整体灾难的一部分。本月初,当库莫宣布纽约市单日死亡人数达到人时,医院,这些数据仅统计了确诊死亡病例数。然而,在4月份的前八天,市法医办公室记录的家庭死亡人数为人。赞比托来到米德伍德公寓的前一天,市法医办公室记录的全市家庭死亡人数为人。3月份,全市每日家庭死亡人数大约才25人。 29岁的赞比托出生在史泰登岛。她曾告诉高中辅导老师,她长大后想当一个殡仪师。“这个理想把大家吓坏了,”她说,“但我就是想当一个殡仪师。”后来,她去了圣约翰大学,因为她意外地发现这所学校居然真的提供殡葬服务的管理学士学位。“当时的心情就是,确实有人把我的理想当回事儿!”她回忆说,“然后,第一次面对我要处理的尸体时,我没有恶心呕吐。” 赞比托毕业后先去了一家专门为纽约市和新泽西的殡仪馆搬运尸体的贸易行。两年前,她来到米德伍德,为两家共享一个办公室和员工的殡仪馆工作:谢尔曼弗布殊纪念教堂(主要服务于犹太顾客)和利索维茨基纪念堂(服务于俄罗斯顾客)。死者的种族或信仰,对赞比托来说无关紧要;她的工作就是为死者人生最后一程做准备,帮助死者的家人告别逝者。她说,她觉得这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它让你感到,自己实实在在地正在为别人做一些事情。” 但是最近,这份工作的意义变了味道。以前,每天最多处理两具尸体;医院太平间的时候,她都会向家属表示慰问;护工会帮她把尸体搬上车。现在,医院太平间里尸体已经堆放不下,有的甚至放到了冷藏拖车里。员工被告知必须严格避免长时间接触感染病毒的尸体。每天早上七点三十分左右,赞比托来到工作的地方都会发现一夜之间又接到了六个或七个收尸服务。她去过布鲁克林,皇后区还有布朗克斯区,每具尸体似乎都与跟新冠病毒有某种联系。她说:“死亡证明上可能没写新冠病毒。但你会看到,死亡原因一栏要么写着肺炎,要么写着呼吸衰歇。正常死亡的去哪了?癌症死亡的又去哪了?还有心脏病死亡的?突然之间,仿佛所有人都是死于肺炎。” 在米德伍德,赞比托和约翰逊两人把尸体搬上货车,但是他们得等到警探检查过尸体照片后才能离开。等在楼下的警官在人行道上来回踱步,尝试打通另一个警探的电话。一小时过去了。虽然超出往日的工作量让赞比托感到前所未有地忙碌,但渐渐地,她越来越觉得迷茫。为了保持社交距离,丧葬负责人不能走进布鲁克林法医办公室,意味着每次她要坐在车里,在停车场等待一个多小时。等医务调查员找到医生签署死亡证明,然后填完死者档案,大概要花数小时。医院太平间的冷藏室里一片混乱,想找具尸体更不容易。用来生成和记录死亡证明的全市电子系统——eVital——也因为过度使用一直崩溃。 终于,警探的电话打通了。警官打开免提。赞比托和约翰逊坐在车里,窗户打开着,竖起耳朵听着电话里的声音。“自然死亡,”电话那头的警探说,“你们可以走了。” 谢尔曼弗布殊纪念教堂 整座城市的太平间 谢尔曼弗布殊纪念教堂是布鲁克林最古老的犹太殡仪馆。年,威廉·谢尔曼(WilliamSherman)在威廉斯堡成立该殡仪馆时,他曾用马匹来运送尸体。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威廉的曾孙乔·谢尔曼(JoeSherman)接过这间纪念教堂。如今,谢尔曼弗布殊纪念教堂在米德伍德的康尼岛大道占据了相当大一块地。大型砖砌结构的建筑,隐约看上去像一樽巨大的棺椁,立面侧有平坦的黑色雨蓬和燃烧火焰状浅浮雕。两辆灵车停放在停车场。自3月中旬以来,场馆内仅允许工作人员进入。“我们现在主要关心的是保护那些活着的人们,”谢尔曼说。 克里斯·卡斯勒(ChrisKasler)是土生土长的贝里奇人,身材魁梧,话语间带着浓厚的纽约口音。,和父亲都是丧葬负责人,他自己也是。“我们家世代从事这个行业,”他说,“我从小就在殡葬环境中长大。”年,卡斯勒祖母去世,享年99岁,是这座城市里最年长的持证丧葬负责人。卡斯勒的两个兄弟也是认证的丧葬负责人,一个是N.Y.U.Langone医院的紧急救护技术员,另一个是美国麦卡利斯特丧葬服务学院的高管。 在谢尔曼弗布殊纪念教堂,卡斯勒在主廊用塑料折叠桌,摆了一个临时工作站。死亡证明整齐地堆放在日历旁。起初,殡仪馆承诺不会拒绝每一个前来吊唁的家属。但谁也没办法预料到现今的状况。以前,再忙碌,一周顶多也就接待12场葬礼。但是仅4月的首周,这里就接收了具尸体。有的必须送去墓地下葬,有的要送去火葬场。墓地和火葬场的两头延误,导致瓶颈出现。比如,市火葬场的下一趟预约排到了两周之后。“现在,这里就像是整个城市的太平间,情况只有更糟,”卡斯勒说。 这里也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遗骸。冷藏室最多只能放下六个成年人的棺材,以及大概四具等待防腐或火化的尸体。卡斯勒每隔三小时就要轮换一遍尸体,防止它们腐烂。他已经把空调温度调到最低:18℃,但仍然比保存尸体所需的温度高许多。两周前,谢尔曼教堂已经暂停丧葬服务。原来铺着地毯,摆放着精致长椅的礼堂,现在被用来堆放46具尸体。有些已经放入棺材,医院提供的橘色“遇难”袋里,还有更多的则放在火化容器——薄纸板箱里。工作人员用警告标签标记那些里边装有感染新冠病毒而死的遗体容器。没过几天,殓房里弥漫着一股酸臭味;工作人员打开门通风时,苍蝇蜂拥而至。 教堂内部堆满了棺材 “这里就像战区似的,”卡斯勒说。在教堂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大块头木棺椁夹在橙色裹尸袋和纸板箱之间。其他尸体要么搁在长椅上,要么搁在墙壁架子上。有一具90岁老妇人的遗体,临时用塑料布包裹着,因为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容器,直到卡斯勒找来一块白色的大毯子,才稍稍体面了一些。卡斯勒说:“对某人来说,她是母亲,是姐妹,是祖母。我努力想把她的头摆正。” 卡斯勒和他的同事们还担心供应的问题。他们的个人防护设备(口罩、防护服和手套等)都快要用完了。医院的时候都至少需要用掉三副手套和两件防护服。赞比托和其他人必须把接触了受感染尸体的物品丢弃。她说,一次标准的尸体运送,在收取尸体的时候需要用掉一套个人防护用品,然后在把尸体放进货车的时候再用掉一套,最后从车里取出尸体搬进停尸房还要用掉一套。谢尔曼已经开始联系其他州的殡仪馆,向他们求购物资。他还需要消毒喷雾剂和消毒湿巾。他有一个堂兄在加州,已经订购了一些物品,准备发给远在纽约的谢尔曼。棺材也不不够用。“来不及生产,”谢尔曼说。 同时,卡斯勒说:“我们只能临时应付。”他在走廊上多摆了两张桌子,其中一张用来安排火葬事宜。他说,殡仪馆内部的混乱局面正在打破他祖母和父亲传承下来的所有传统。卡斯勒说:“遗体也需要被体面地对待。你对待死者的态度与你的成长一脉相承。”说话间,他接到一通电话,然后匆忙离去。半小时后,他发来短信,说:“我的侄子刚刚医院。已经确诊。呼吸困难。” 生与死之间的最后一程 4月14日,纽约市卫生部修订了上个月的确诊死亡病例统计。根据先前的估计,新冠病毒确诊死亡病例为例左右;现在,另有例未曾确诊的患者,也死于新冠病毒。“纽约人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engyuehana.com/syhyy/10812.html
- 上一篇文章: 天津港到萨凡纳海运如何将货物从天津港海
- 下一篇文章: 全球15座最值得去的灯塔,每一座都是世